这些关于艺术的思考,被法国天才历史学家基佐收录于著作《艺术论》中,《艺术论》是一部他在全世界范围内搜集各种神奇的艺术品过程中所作的笔记,一部关于艺术理论、艺术鉴赏方面的经典著作。书中探讨了各种艺术之间的关系和差异,同时又因包含了对某些历史细节的描述,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他在本书中对自己曾研究的各位大师的作品进行了筛选,只保留了那些他认为或是因为画中的名人要事,或是因为其在艺术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仍然使人感兴趣的作品。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研究,他颇具个性地阐述了绘画、雕塑与雕刻之间的关联和差异,其中主要评述了意大利流派和法兰西流派的画作。
基佐的助手乔治·格罗夫在基佐的指导下,将此书译成英文。近日由广西师大社新民说推出的《艺术论》中文版正是基于基佐认可的权威英译本,这也是《艺术论》的中文首译本。今天为大家分享其中一篇,介绍关于绘画与雕塑的异同。
在一个人们拥有的激情和天赋多于判断能力的时代,雕塑和绘画艺术是两个长期充满热烈争议的课题。争议的目标是要确定这两种艺术形式谁更胜一筹,而这种争执是由于最深刻的轻蔑和最旺盛的妒火引起的:画家们和雕塑家们已厌倦了这种徒劳的细致工作——在自身艺术形式的历史、目的和工艺中发掘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的某些优势准则;于是,中世纪时期的人们太容易忽略一种争议是否适当,而只顾将它提出,这使得那些能人巧匠们会在毫无价值的争论当中消耗他们的时间,而且还认为这种争论价值巨大。
在今天,如果听说一位雕塑家为了证明自己的艺术有多么杰出,而赞扬一个人用黄金制作雕塑雕像,用白银制作绘画雕像,然后分别将它们放在左手和右手的这种想法,将会引起莫名的惊诧。如果我们听到有一位画家急不可耐地驳斥这一具有说服力的论据,说这种“炫目的金羊毛”(golden fleece)只是一头愚蠢绵羊的外套,因此雕塑除了是一门可怜的艺术,可能什么都不是,哪怕这尊雕塑是黄金制成的,我们也会同样惊讶。然而,在15世纪到16世纪,这些贤能之间确实进行过这样的争论,而且在博塔里的《艺苑名人书信集》(Raccolta di lettere sulla Pittura Scultura, etc.)中占有相当篇幅。瓦萨里觉得有必要详细记录这些争议,而尽管他理智地表示过对这种争议并不赞成,但他仍郑重其事地进行了记录,而且表达了他的观点,就好像这件事情的性质非常严肃一样。
就像许多其他重要问题那样,关于绘画和雕塑谁更胜一筹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至少这种无谓的争执已经停止了。相对于自己不了解的艺术形式,雕塑家和画家无疑还是更钟爱自己从事的艺术,但他们已经不再认为有必要将自己从事的艺术捧到高人一等的地位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已不会再去探寻雕塑是不是一门比绘画更尊贵的艺术,但我们确实会致力发现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共性、差异,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能够或者不能互相借鉴的,它们各自的独特领域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又是什么,还有它们各自应致力的特定目标是什么,它们各自不能熟视无睹的特定目标又是什么。对这些真正重要的问题的讨论,于我而言就好比为艺术的本质撒上些许光辉,希望能有助于艺术家们在他们所从事的艺术上取得独树一帜的成就,而且让业余爱好者能乐于将他们的评价建立在坚实理性的基础上。
在为艺术呕心沥血六十多年,耗费了大量精力和智力而产生了巨大影响后,米开朗基罗逝世了。他留下了许多弟子,他们意识到老师已经离去,决心跟随这位长期引导着他们的伟人的脚步继续前进。这一画派的所在地佛罗伦萨只留下他们老师的少数画作,大师本人一直对油画不屑一顾,据他所说,“(油画)是为妇人和懒鬼所作的艺术”。米开朗基罗的壁画杰作都在罗马,而且那幅他在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竞争时设计的著名壁画可能是因为偶然事故,也可能是因为巴西奥·班迪内里的嫉妒而被毁掉了。于是,他创作的那些雕像几乎就成了那些尊崇他的弟子们能寻访到的仅有的学习模板,而他的弟子们也一直满足于模仿这些雕像。他们满怀热情地研究那些雕像,给这些雕像赋予自己的想象力,在其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品位。于是乎,佛罗伦萨出品的绘画通通呈现出大理石般的刚毅线条感,其原因别无其他,只是因为这些画作保留了对雕塑的研究结果。
兰齐说道:“在他们的某些绘画中,你会看到一群人物一个接一个地挤作一团,面无表情。半裸的人物唯一的目的好像是为了表现类似‘维吉尔笔下的恩特鲁斯’(Virgil’s Entellus)那样‘孔武有力的筋骨’。迄今为止都用可爱的蓝色和绿色的地方,你会发现一块浅棕色,单薄的浅色代替了列位大师曾使用的饱满颜色,安德烈·德尔·萨托(Andrea del Sarto)时代研究甚多的重要的浮雕式绘画技术似乎被完全忽略了。”
这样的结果——在艺术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过——足以证明对雕塑的模仿使画家身陷犯下严重错误的危险境地。我们刚刚列举的佛罗伦萨画派画家们犯的这些错误,其原因并不在于对米开朗基罗雕像进行特定的专题研究;他们可能从米开朗基罗那里学到了某些表现人体构造知识的夸张手法,而他们最大的错误是对那些雕像进行全盘的学习和模仿。这个事实——意大利人自己是承认的——如果被正确理解,将为我们研究那些造成类似恶果的各种因素提供起点。这些恶果源于各种艺术形式的本质,而由此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
流传至今的说法是,雕塑的目的是表现人物的外形,而绘画则是为了表现人物的整体外观。这种说法在我看来还远不够准确。不能说画家就不需要处理外形问题,因为他也要描绘出人物的轮廓,而且,当他努力在画布上展现人物投影的时候,还必须赋予人物如浮雕般栩栩如生的外观。因此这两种艺术形式在目的上非常相似,但也存在重要的差异:它们的掌控手段截然不同,且它们达到目的的途径也不一样,没有任何交叉点,也不会重合。
雕塑家会先收集好一堆黏土,模特在他眼中就像柏拉图所说的原始人在上帝脑海中那样:他聚精会神地围着模特转,前后左右从各个方向检视模特,而且要完整地测算模特的尺寸。他还要了解模特的结构,包括外形、高度、骨骼的厚度;他需要知道骨骼是如何连接成一体的,还有每一块骨头附着哪些肌肉,又是如何运动的。雕塑家最初的行动是建立好对整个骨骼构架的印象,然后用肌肉覆盖骨骼,从而得出塑像所需的姿态和动作幅度,最终给整个塑像覆盖皮肤,从而完成人体各部分的比例,并且赋予一种生动的人物造型。
这就是古代雕塑家向我们呈现普罗米修斯塑像这种艺术瑰宝时的艰辛过程。当大理石取代黏土,而且经雕塑大师之手巧夺天工,赋予其生动的人体面貌外形时;当雕像表面已经呈现出皮肤的细微起伏,而且这样的皮肤构造简直可以以假乱真,让我们忍不住去猜想“皮肤”下面的人体组织形状时;当这些真的完成时,就会发现那具石人和它的活体原形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实质内容、颜色和重量而已,而且实际上它甚至已经拥有人体外部形态的一切细微特征。
另一方面,画家的目标是要在彩色颜料的帮助下,将人物形象绘制在平面上,使之能向观众呈现出一种从一段距离之外看上去栩栩如生的效果。由于眼睛一次只能看到对象的一侧而已,而且这一侧并不是一个平面,而是和眼睛正对着的人物的那一部分,这部分的轮廓由一条将人物的可见部分,或者说前侧,与视野之外的后侧部分分离开的曲线组成。这条轮廓线就是画家领域的界限,正是轮廓线构成了画家绘画对象的外形,而且此后画家的艺术就是在画布上轮廓线以内的部分进行填涂,真实对象的相似外观是通过相应轮廓内所勾勒出的内容表现出来的。
因此绘画建立在一种光学法则上,这与我们在自然条件下根据事物轮廓的变化,还有光与影的明暗作用,来判断其距离、外形和突起部位的法则是相同的。
此外,画家要像他在自然界中所发现的那样去表现明暗分布效果,要像它们原本所展示的那样给绘画着色,并且通过色彩的分布落差来调节明暗,或者通过描绘增亮的光线和遮蔽的阴影来修饰颜色,从而赋予画作以多种多样的色彩。正是通过这些手段,画家得以忠实而逼真地表现他所致力去表现的对象,而同时这也是他所从事的绘画艺术的终极目标。
看来雕塑和绘画两种艺术的性质存在差异,各自独有的领域和掌控手段也存在差异。我们发现它们之间的唯一共同点在于构思。但也存在这样的差异:雕塑的构思理念在于从高、宽、深三维塑造人物的完整立体形象,而绘画只能限定在高和宽的二维构思上,深度或者说投影则要通过阴影、光线和色彩来表现。
基佐,不仅具有作为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敏锐,同时也有非常高的艺术修养。这是一部他在全世界范围内搜集各种神奇的艺术品过程中所作的笔记,关于艺术理论、艺术鉴赏方面的经典著作,书中探讨了各种艺术之间的关系和差异,同时又因包含了对某些历史细节的描述,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他在本书中对自己曾研究的各位大师的作品进行了筛选,只保留了那些他认为或是因为画中的名人要事,或是因为其在艺术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仍然使人感兴趣的作品。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研究,他颇具个性地阐述了绘画、雕塑与雕刻之间的关联和差异,其中主要评述了意大利流派和法兰西流派的画作。
本书插图丰富,同一幅作品,分别配有版画和原画,在这种对比之中,令人仿若置身于一座美术馆,亲临其境地感受到画作中震撼人心的力量。
本次翻译选择的底本为基佐的助手乔治·格罗夫翻译的英译本,是在基佐的指导下译成英文的,经基佐认可的权威英译本。同时本书为中文首译本。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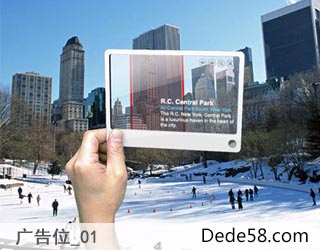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